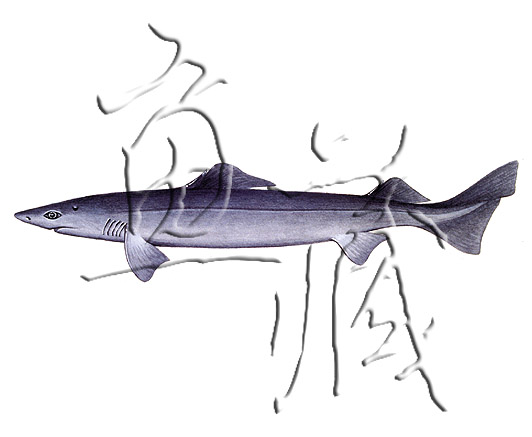廖中山
我叫廖中山,家住新店,目前在基隆海洋大學海運學院航海技術系教書,為響應呂秀蓮女士舉辦的「一九九一我愛台灣年」活動,我願意將個人經歷和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過程及一些雜感,做為思考台灣問題時的採樣樣品。
首先由我的身世談起, 1934 年陰曆 6 月 19 日,我出生在河南南部小村子,抗戰勝利時,我真正的教育程度還不如現在的國小學生, 12 歲離家在江南流浪,隨後參加海軍陸戰隊,在 1950 年元月轉到台灣。 1959 年調入陸戰隊黨務單位,從事文書工作, 1955 年考海軍官校, 1959 年 12 月畢業,畢業前生肝病,所以畢業後沒有上船,留在官校做助教,隨後考海軍專科學校,讀一年後,肝病又犯,住了兩年的療養院,在 1963 年 7 月奉命退役,官階是海軍中尉。
退役後在屏東教書,並結了婚,教書 4 年後因生活上的需要,參加了航海人員上船人員的考試,在 1967 年開始了跑船生涯,至 1973 年放棄生活不安定的海上工作,到高雄海專教書,因為在校期間對航海學有興趣,在 1974 年以《實用航海天文學》處女作,通過講師資格的審核。 1977 年升副教授。 1980 年將出過的四本有關電子航海的書,整合成一本「電子航海學」完整的電子航海體系的教材,順利通過教授資格,再調任航海科主任。 1982 年學年度調海洋學院教書, 1983 年將家從高雄搬到台北,這是我整個求學、工作直到生活安定的過程。
我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成長,約可分為四期:
第一期從 1949 年到 1957 年,是幼稚期。在這段當兵入黨的日子中,我將自己定位成類似紅衛兵的類型,自己稱自己是「藍衛兵」。在意識形態上由一片白紙染成極端的忠黨愛國、效忠領袖的類型。思想完全是宜線式的,在部隊中辦黨務,官校同學視我為黨棍子,是危險人物。
第二期則從 1957 年到 1973 年,我稱之為懷疑期。這是從官校二年級開始,對以前立的理開始懷疑,起因是為了一位由越南來的同學在生了眼疾之後,轉學到台大去,沒有像別的同學一樣回到部隊,當時自己認為不公平,也很憤怒。對聽到的信念開始懷疑,但還沒有失望,隨後在軍隊中到處放砲,畢業時得到「心胸狹窄、言論偏激」的評語。在跑船時,又因沒有時間做自我人格的教育,對一切事物都感到相當悲觀,且有很深的感觸。
第三期從 1973 年到 1983 年,我自稱為轉型期。是意識形態上的轉變,這是在生活安定下來後,自我反省,對於自己所受的革命教育及對任何事都是標準答案,對人性尊嚴和民族意識毫無所知的情況,感到相當幼稚,於是開始在休閒時間讀一些書籍刊物。看的範圍很廣,從武俠、科幻到雜文都看,最早看柏楊的文章,從柏楊、孫觀漢等的文章,讓我懂得如何去思考問題,對同一件事情,從不同的角度去思索。隨之看李敖的文章,使我對中國國民黨史有深入的了解。推翻自己以前建立的體系,對一些黨國元老、民族救星的看法,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,從極端崇拜到極端厭惡,甚至到仇恨的階段,這是我所謂意識型態的轉變期。
第四期 1987 年至今,是我的自立期。就是自己能夠站起來,自己獨立思考,我到英國讀一年書,出國前接觸到鄭南榕先生辦的時代雜誌,除了出國的那段時間,可以說是從第一期到結束每期都看,然後思考,我對台灣開始關心,就是從鄭南榕的雜誌裡面的報導啟發,在意識形態上,從大中國的、故鄉的情感,轉而寄託到這塊土地和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,對這塊土地的認同,就是從 1987 年以後,建立了自己獨立思考後才有的認知。
最後一部份我所要談的,是我對如何愛台灣的一些思考。
第一點是我對愛的體認。記得曾在孫漢觀書中看到兩句話:「有心的地方必有愛,有愛的地方必有美。」對於第一句話我很能夠理解,就是說一個人處處留心,把心放在某個人、事、地、物上,自然會產生愛。但對於第二句話,當時的我無法理解,在我膚淺的想法中,真心誠意愛某件事,不慬不美,而且相當痛苦。但從近年來台灣所發生的一些事情,我像霧裡看花般,慢慢地體會到這句話的真義。以鄭南榕先生為例,鄭先生在他女兒鄭竹梅出生時,他用一整天的時間思考,面對當前台灣日益惡化的人文、自然環境,身為上一代的人,有絕對的義務為下一代創造最好的生存環境。但在千頭萬緒中,他認為應先從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做起;所以,他僅僅為了實踐這個理想,選擇了死亡。看似非常殘酷但我好像能夠體會他心中的愛與美,然而這種美或是淒慘的、旁人無法做到的,愛不是浪漫的,真實的愛是經過極端的痛苦、極端的艱苦磨練出來的,像施明德、黃華、林義雄、鄭南榕等人的際遇,可感受到「有愛的地方必有美」,愛必須從真心關懷開始。在中國幾千年打打殺殺中,我體會不出像這樣沒有階級性、真誠對待愛,因此,我覺得在台灣有這麼自美的榜樣是件很可喜的現象。
第二點是我對家的追尋。我是一個自幼離家流浪的人,在成長過程中,特別望有個家。而我的妻子出生於高雄,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,在她 14 個月大時,父親代表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要塞司令部談判, 5 個進去的人,只有 2 個出來。她父親被害時,只留下她和比她大 2 歲的姊姊;在經過八年孤兒寡母的艱苦日子後,她的母親自殺身亡,當時她才九歲。因此,內人可說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,我比她稍幸運,我是個有父母有母的孤兒,因此,我倆都期望有個家,對我們而言,家不只是個地方,還必須有情、有愛。去年暑假我倆去探望一位好友當兵的兒子,由於我這位朋友夫妻感情不好,這個孩子看到我時,曾感慨地告訴我,他在軍中想家,放假回家時也在想家,面對家園的體認,竟教人很徬徨。前些日子看到一則消息:陳若曦之子在美宣誓,要去波斯灣打仗。一個中國人宣誓為另一個國家效忠,那國究竟在哪裡?去年我回大陸老家一趟,卻感受不到 40 年來朝思暮想的家的感覺。多少年來對台灣,我自認無法成為內人,在外省人的圈子中,我因為沒有身世背景,感受不到平等的親情關懷,自覺像個外人,但在本省人的圈子中,又因省籍的隔閡,而感受自己是個外人,究竟如何使自己成為內人,幾乎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。
第三點是我們打算怎樣去愛台灣。這應分二個部份來說。首先我覺得要設法拆去自己心中的柏林圍牆,所謂內人、外人都在自己一念之間,如果我自己認定自己是台灣人,我就努力去做個台灣人。同理,目前有些人自認是中國人,我們尊重他的意願,但要做個中國人應要到中國去做。要移民出國,我們也同樣尊重祝福。當然還要牽涉到敏感的台獨問題,但一個人愛鄉土,並不涉及政治問題,而是做人起碼的條件。在我的觀念中,現階段我先愛台灣,在 57 年的生命中,有 42 年在此度過,我應自認是台灣人,不管周圍是否接受,也不管別人會不會排擠,我從 1987 年開始真誠的要做一個台灣人。
其次,是目前台灣人際關係應如何建立。一般人所謂禮讓、寬容等說法,說來容易,做起來很困難,在中國老家時,二哥談到一句家鄉的俗話:「若要公道,先要顛倒。」也就是說凡事先要替別人想想,以省藉情結為例,不可否認外省人在工作上有排斥的現象,但反過來說,任何人做老闆,必是先用自己人,再考慮用外來人,何況 40 年來,台灣整個政經的支配權都掌握在外省人手中,而從二二八延續下來的,是多年的白色怨情,絕大部份民眾看到的,是一種利奪和迫害,因此所有的外省人若站在這個角度想想,就可以理解為何台灣人有些偏激的心態。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看,台灣有 1/5 的人口籍貫是外省人,而這些人有 95% 和本省人一樣要盡服兵役、納稅的義務,只有 5% 的外省人享有特權。而外省人在此不僅未受到特別照顧,在遭受懷疑時,境遇較本省人更為淒涼,白色恐怖 40 年中,外省人受迫害、被屠殺、無端失蹤的例子亦無可計數。本省人受迫害,尚有親友相助,外省人受迫害,則無地申訴。本省人應該站在外省人的立場想想,才能夠慢慢地修正自己的心態,互相尊重。當然,愛台灣有可能遭迫害,愛中國卻會成為英雄人物,但各人有各人的原則,愛中國就應該將根移去中國,在中國完成統一後,再回來造福台灣。身在台灣,就應腳踏實地地付出對這片鄉土的愛。
第三,要愛台灣就要認識台灣。現在的台灣人不了解台灣的歷史、地理、山川、河流,甚至台灣整個文化的演變,特別是風土民情方面,認識非常有限。以語言來說,一般人認為台灣話是屬於低階層的用語,但我去聽李鴻禧談台語之美,以及聽呂秀蓮解說台灣民謠時,感受到那種比中華民族漢文化更為古典的文化。因此,要愛台灣,就要先認識它,再慢慢產生愛慕,就像人與人之間產生的感情一樣。如果有愛,即使缺點也能成為優點,也能是一種美,但先決條件是先要認同,才能夠徹底認識了解。
第四點,是應該建立台灣新的文化,不可否認的,除原住民外,所有台灣人都是漢民族的後裔。然而,就文化層次而言,我覺得台灣正走向自己的文化,從漢文化轉成新文化。就像鄭南榕、林義雄這類的犧牲,及許多留學國外的高階知識份子,放棄較優越的生存權利,而選擇回來愛台灣,還這正是一種新文化的形成,這種對生命價值觀的改變,為了愛台灣,寧可忍受比死還要痛苦的自尊上的迫害,這種對追求自尊的美感,就是新文化的形成。這種新文化,是從大陸文化那種具擴性排他性的心態,慢慢轉向海洋文化,產生尊重、包容性特強的心態,這是非常可喜、可愛的趨勢。
最後,我們必須了解的是,愛並不是一種浪漫,尤其對台灣的愛,在現階段只是有相當的危險性。這種危險性,輕則在團體中受排擠,嚴重點會失去工作,最嚴重的狀況是要付出生命,付出人性的尊嚴。因此要愛台灣必須有相當的心理準備,要明白這份愛可能要有某種程度的付出。以我個人為例,我希望能在 65 歲平平安安的退休,但若因對台灣的愛,使我無法達成這個願望,我也就認了,因為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,很難說我愛台灣了。
(原載於 1991/2/13 自由時報)